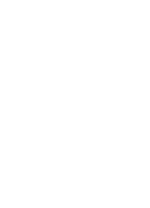2014年7月19日,央視主持人白巖松出席了“北京大學醫學部醫藥衛生管理論壇暨北醫醫院管理高級研修項目百期校友會”,并作精彩演講。面對數百名醫院管理者,白巖松鮮明地指出了醫生職業在社會中的五重價值。
七年前,因為踢球骨折,我在北醫三院做骨折手術。在手術臺上,大夫問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
當時,我的回答是:“我會做一個模范患者。這是您的專業,一切聽您的。”手術效果非常好。在手術半年后,我回到了北醫的大院踢了一場足球,為我做手術的醫生也在場。
其實,當你信任對方的時候,對方給予你的會更多。當你一開始就帶著懷疑的眼神時,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當下中國,醫生和整個社會之間正是處于這樣一種錯位的關系中。

這個行當介于上帝、佛與普通職業之間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談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醫生?醫生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
大家說到醫生,都會說兩個詞,一個是醫德,一個是醫者仁心。
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有哪些行業的后面是帶“德”字的?只有教師和醫生,一個是師德,一個是醫德。我們的前人夠聰明,之所以這兩個行業后面帶“德”,因為他們維系人生中兩個最重要的健康領域,一個是精神健康,一個是肉體健康。所以,社會對這兩個職業的要求特別高。現在很多的醫生都有委屈:我在做這樣行善積德的事情,為大家守護健康,可是還面臨著懷疑。千萬不要懷疑,千萬不要有委屈感。我還是要強調,你越靠近佛,你遭受的磨難和委屈就越多。因為你的職責大,大家的期待也就越高,大家對你的需求也高。
醫者為什么要有仁心?醫生這個行當介于上帝、佛與普通職業之間。大家到醫生這兒來,往往是帶著苦痛,帶著絕望。歸根到底,與其說是到醫生那兒來看病,不如說是到醫生那兒來尋找希望。我們常說,醫生是治病救人。其實治病就夠了,為什么還要說救人?治病只是治療病狀,但是救人是一個綜合的概念。我們面對這個行當的時候,過多地強調生命的因素,而忽略了心靈的因素。這也是社會上很多的需求跟這個行當發生摩擦的誘導因素。
干醫生這個行當,你看到的總是一顆又一顆苦痛的心,一張又一張苦痛的面孔。當然,醫生最大的幸福是,病人來的時候是苦痛的表情,經過你的治療,一段時間之后,他帶著笑容離開了。因此,心靈的撫慰和支撐原本就是這個行當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而不僅僅是五年六年學到的醫術本身。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療技能和心理上的撫慰加在一起,才構成“醫者仁心、治病救人”這八個字的全部含義。
醫生這個職業具備五重價值
醫生的價值體現在多個方面。比如說,中國人用四個字把這一輩子概括:生老病死。請問,這四個階段,哪一個階段離得開醫生?請告訴我,哪個人能夠確定一生都不會成為病人。如果你能確定自己一生都不會成為病人,你就罵醫生吧!沒有任何人敢打這個包票。
從醫德到醫者仁心,再到治病救人,都體現了醫生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價值——生命價值。
醫生僅有生命價值嗎?我覺得醫生還具有社會撫慰價值。患者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折磨,釋放往往來自醫生的撫慰。因此,一位好醫生的標志是治好病,也包括讓很多人感受到希望和溫暖。這原本是另一種醫術。醫生第二個價值就是撫慰整個社會。
我覺得醫生的第三個價值是情緒價值,第四是社會的信心價值。所謂情緒價值,社會上戾氣、抱怨幾乎到處都有,如果大家能夠有一個健康的心態,擁有一個健康的人生狀態,醫患沖突就會減少。所謂信心價值,我們中國現在什么都不缺,但是最缺的就是信任和信心。醫患關系失衡的核心就是信任缺失。如果這個行當的改革能夠進行得更加徹底,恢復信任,就會對社會產生巨大價值。

另外,2013年末,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人數第一次突破2億,今后還將以加速度增加,老齡化對醫療的需求將是巨大的。我認為中國到了提出健康壽命的時候了。
這和醫生有什么關系嗎?那就是醫生的另一個價值——科普價值。寫一篇論文和醫生的晉升是有關系的,但是寫十篇科普文章卻對晉升沒有影響。請問有多少醫生愿意做這樣辛辛苦苦的事情?除非他有極大的道德追求和責任。但是每一個醫生都知道,科學常識的指導,會幫助相當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急病不轉化為慢病。
生命價值、社會撫慰價值、情緒價值、信心價值、科普價值,我認為,醫生這個職業具備這五重價值。但現在醫生被整個社會安排了太多的應急價值,一到流行病傳播的時候,一到汶川地震等災難發生的時候,醫生全成了白衣天使。因為關鍵時候醫生是社會安定的穩定器。但是一過了那段時間,大家就都健忘了。然后,又開始罵醫生。
關鍵看環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還是惡
我前幾天也出席了中國醫師協會醫學道德委員會關于醫生道德自律的會議。道德的問題需要有力地倡導,但是僅靠倡導和自律是不夠的。中國人的人性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比一百年后更好,關鍵是看環境激活的是人性中的善還是惡。
今天中國的道德問題似乎太大了,比如老人跌倒了沒人扶。老人跌倒了去扶他(她),他(她)會訛人嗎?我相信十個訛人的老人中有八個九個都是善良一生、謹小慎微過來的中國人。但是,在中國,老人們第一怕的就是給孩子添麻煩。當他一摔倒,一發現動不了了,立刻擔心給孩子添多大的麻煩,價值觀一下子就扭曲了。這時候,任何人伸出一只手,他們都會像救命稻草一樣抓住,說不定就會訛人。等我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健全了,我想這種情況就會很少了。
因此,道德問題往往是改革不到位的問題。幾十年前,中國兩輛汽車一撞,下來就打,為什么啊?因為打贏打輸決定了賠償。今天,兩輛汽車一撞,沒有人動手,因為每個人都強制上了第三方責任險。可見,制度可以提升文明。
如果一位醫生一上午看五六十個號,水都不敢喝,廁所都去不上,如何做到耐心地傾聽每一位患者的聲音?如果做一個手術才得一百多塊錢,但一個支架利潤可能幾千塊錢,你會作何感想?要是在自己醫院做一個手術只有一百多塊錢,走穴去另外一個醫院,可能拿到一萬多塊,我們有什么資格要求人性在這樣扭曲的制度里必須高尚?坦白地說,目前社會上出現的相當多的醫患矛盾,是在替醫療改革行進速度太慢背著黑鍋。如果醫療改革不能快速地破局,這個黑鍋還要背很久。
不能把壓力全部推到醫生和院長身上
最后,在緩和醫患關系上,整個社會,包括媒體,應該做些什么?
我認為,首先第一點,堅持改革。每次出現傷醫事件的時候,我都要發聲。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說話,是在替每一位潛在的患者說話,而不只是在替醫生說話。醫療改革如果不快速破局,醫生的黑鍋會背很久。
接下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希望能夠建立新的尊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連續幾年提議設立“醫生節”。我在提案里有這么一句話:尊重是另一種約束。我們已經有了教師節、護士節,為什么不設立醫生節?設立醫生節,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種約束。
第三點則是,就事論事,不要迎合情緒。相當多的醫生對現在的一些媒體報道不滿意。媒體也有它的市場壓力,我們無法排除某些媒體人從迎合社會情緒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報道準則,但這是短期策略。長期來看,他們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個醫患沖突案件都應該就事論事,不能擴充成社會對立情緒。
第四點,法律要跟進。我希望能從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紅繩。出了事情就把靈堂搬到醫院大堂的行為,必須杜絕。
第五點,我也要提一下,醫學是科學而不是神學。現在社會上彌漫著一種情緒:我把病人交給你,你必須給我治好,不能出任何問題。請問,哪個醫生能夠做到?雖然現在醫學已經進步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疾病也在發展啊。我們應該讓全社會都知道,目前有相當多的疾病,可能被控制、可能被減輕,但不大可能被治愈。

科學本來就是有成功、有失敗、有探索,還有曲折的。但是,現在的醫患關系背景下,很多醫生都不敢建議患者用冒險的治療方案。社會需要一種潤滑機制、調節機制,不能把風險和壓力全部推到醫生和醫院院長身上,否則沒有醫生會選擇去為患者冒險。
一個良善的社會應該提供良好的潤滑機制。我去臺灣采訪,一進醫院,就有志愿者服務站。幾乎每家醫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們都會領著你到各個部門,你的焦慮就會減輕。這些志愿者全都是經過培訓后上崗的,一個禮拜只需要在醫院待兩個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們是否也能建立這樣的機制?
所以我認為,中國醫療困局的突破,需要整個系統的改變。我們全部的情緒都寄托在每一位醫生溫和地對待患者上,這其實做不到,我們依然沒有進入良性循環。潤滑機制和緩沖地帶非常重要。我們在座的院長,可以嘗試在醫院設置志愿者,引入NGO (非政府組織)。他們并不占用你們的資源,只是要有一定的培訓,就可以完成長久的潤滑和緩沖。
為什么我對醫生有這樣的情感
最后我要講一個故事,作為結束。為什么我對醫生有這樣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經歷過這樣一件事。
我大學畢業回老家,即將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媽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我的家鄉在內蒙古的海拉爾。那個地方很偏遠。上世紀70年代,我爸那時30多歲,總咳嗽,有時還帶血。有一天,他出差要去天津。我媽就囑咐他,辦完公事一定要去醫院看看病。我爸去了天津,最后一天才去醫院。結果,他被診斷出有癌癥,醫生不好當面告訴他,只是對他說:對不起,你不能走,必須住院。
我爸肯定不干:一堆事情,必須要回去。他掏出車票對醫生說,這是我今天回海拉爾的車票,非走不可。醫生就說,請你稍等,我去找我們的領導來跟你談。醫生去找領導的時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車站等車的時候,火車站的喇叭響起來,居然有人找他:海拉爾來的某某某,請到火車站門口。我爸走到火車站門口,下午那位醫生,焦急地站在門口等他。原來那位醫生記住了晚上的車次。我爸就這樣被救護車拉回了醫院。
盡管我爸兩年后還是過世了,但是我媽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安安靜靜地說:“如果遇上這樣的醫生,加上現代的技術,也許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2020華為手機杯中國圍甲聯賽第十一輪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
2020華為手機杯中國圍甲聯賽第十一輪 西藏阜康 VS 上海清一